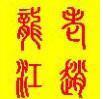一束温暖的火苗
一束温暖的火苗
文/赵富
在童年的记忆里,泥火盆是我心中温暖的种子;至到老年,每当想起童年里的泥火盆,心里还充满着热融融的暖意。
那个年月,冬天一迈进庄稼院的门坎,外边的天气嘎巴嘎巴的冷,低矮的小房内也冻得伸不出手来,坐在炕沿上唠嗑都得操着袖,山墙角挂上白刷刷的霜,象个白胡子老头在那疙瘩蹲着,就连晚上尿盆子都结上薄薄的一层冰茬。
在五、六、七十年代,庄户人家的十冬腊月,没有一件采暖设备。火墙,没有;炉子,没有;暖气,没有。一到晚上,人人躺在炕上,靠一铺大火炕散出的热能驱寒;每当白天,个个坐在屋里,又仅靠炕沿边摆着的泥火盆取暖。而泥火盆,就算是全屋子里唯一的一件采暖“容器”了。虽然土点,原始点,但在冬天里,也照样温暖了一代接一代的庄稼人家。
泥火盆是谁发明的,没有留下历史痕迹;泥火盆又是从那个朝代传下来的,也没有发现谁去考证。但有一条可以肯定,小小的泥火盆,也确确实实地凝聚着庄家人生存的、御寒的聪明和智慧。( 文章阅读网:www.sanwen.net )
泥火盆是黄泥做的,我发现第一个做火盆的匠人是母亲。那时,农村冷得出奇,屯子穷得吓人。不过,老天虽然寒冷,生活虽然贫穷,却塑造出母亲坚毅刚强、吃苦耐劳的性格。在夏天,她用的勤劳的巧手,做成美观适用的泥火盆;在冬天,她把泥火盆从仓子搬到炕上,装满燃烧的苞米羊子火碳。我家兄弟姊妹多,个个肩挨着肩,我的母亲照一般的母亲付出的艰辛要多得多。但母亲每多付一份艰辛,就是多换来的一份亲情的爱,就象热乎乎的泥火盆散发出的热能似的,呵护温暖着我们衣着单薄、象小鸡雏似的一群孩子。
做泥火盆是需要技术的,并且还需要有“美学”的艺术细泡的。心灵手巧的人,是属于会做的,其泥火盆摆在炕上,秀气大方,象个上档次的泥塑作品;笨手笨脚的人,是属于不会做的,其泥火盆摆在炕上,三扁四不圆,又丑又土,象个很低劣的的泥堆盆罐。而母亲做的泥火盆,在左邻右居是出了名的,时不时地还被请去献艺指导,但劳动和手艺都是无偿的,只是换来大娘大婶们一阵阵通俗的笑声。
做泥火盆的工艺程序是严谨的,一环扣一环,环环紧扣,一个环节出毛病,就会影响整体。首先选季节,春天和秋天较好,空气干燥,湿泥易干。模具一般都是用瓦盆(二号的)当,盆口扣在一块平整的板上,把泥抹遍瓦盆外,约1公分厚,用小铲压实提光。泥是粘黄土和的,羊究为少许麦余子,还要剪些乱麻丝碎头,发酵个三五天方能糟好。当往二号瓦盆的模具上抹呼的时候,还要缠上很多圈成根的麻匹子,用小铲压挤到泥盆的邦壁体内,起到钢筋砼里“钢筋”的作用,待泥火盆干后,拉力较强,整体性好,结实耐用。做泥火盆的沿是个功天,按照模具二号瓦盆散出的沿,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把泥捏好,其样式与盆壁的风格协调一致,还要把盆壁的麻丝“拉筋”延伸到沿上,否则使用时就会掉“下巴”。做底时更需要匠人的想象空间,因模具是平底,而泥火盆的底要做出个碗状,即要捏出底沿,还要整体一致,更要结实耐用,来回移动泥火盆时是最费底的。待泥火盆八分干后,母亲就把垫板扣过来,让盆口朝上,再把二号瓦盆模具提出来,母亲说,全干了再提模具,是易把盆壁沾坏的。在呼泥之前,母亲把模具抹点豆油什么的,就象建筑术语叫“脱模剂”似的,母亲说,要不脱模时是要粘模的。起模之后,母亲对个别没提好光的地方进行找补,她用一个小玻璃瓶,一点一点地赶压,有时抽着烟袋,一口流水吐到盆壁的麻面处,然后再用瓶子一赶,光亮一下就出来了。全部工艺完成之后,泥火盆便放到阴干的地方,让它自然干去,母亲说,爆晒易裂。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现母亲做泥火盆的情景。当时人小,不懂得其中有读不尽的情丝,只认为这是天下母亲的一项必须做的“功课”。后来长大了,阅历丰富了,我才逐渐懂得这门“功课”的深奥。原来,这是母爱的火,凝聚在泥火盆里燃烧,烤暖了儿女们滚烫的心。
俗话说:三九四九,打骂不走;腊七腊八,冻掉下巴。我们小孩子在家是呆不住的,不管天气能否冻掉“下巴”,也要到外边去玩。记得一次,下“大烟炮”,我没戴手捂子,小手冻得象猫咬似的,跑回来就伸手去烤火盆。冷不丁的,母亲一下把我拉过到外地,从门外抓一把雪就往我手上擦。雪一挨手,那滋味刺心一样的疼。母亲告诉我:以后记住,你看你大拇手指肉皮都有发白的一块,是冻得不过血脉了,一烤就会出现冻伤,年年冬天是要犯的;不过,只要你不烤火,只用雪一搓,开始手指热乎燎的,呆一阵就恢复原样了。母亲的朴素道理,我用了一辈子,又传给了她的孙子、孙女。
那时的孩子,大多是没有衬衣衬裤的,有个小裤叉子也算不错了。在寒冬腊月,又在屋里猫不住,到大道上玩一会,脊梁骨搜搜地瓦凉。回到火盆前,母亲先让我烤后背,嘴里还一个劲地叨咕:火烤胸前暖,风吹背后寒。一烤后背,果真血压上来了,血管流速快了,就觉得浑身热乎乎的。不知这法用在别的孩子身上灵不灵,反正每次用在我身上就是管用。
从灶坑掏到火盆里的火,柴禾要用硬柴禾。但柴禾不能烧透,要在柴火还冒点虚虚的青烟时就撮到火盆里,然后压实闷上,如果有时青烟多了,是很呛人的,就放在外屋地上多冒一会。多是用苞米羊子的火、豆杆的火、毛嗑杆的火、羊草的火、树枝子的火,这些算是硬火,但最不好的火是苞米杆子的火、麦滑溜的火,因当年的苞米杆子有青杆子烧不透,丁巴冒烟,而麦滑溜的火太软,一沾风就成灰。
扒拉泥火盆之火的工具,叫烙铁,印象中是铸铁的。长大后看电影,又好象与那电影的刑具差不多。但在我们家中,烙铁的功能可就大了。母亲抽烟点火,用烙铁;母亲灯下润布衬,用烙铁,就好象是现代的润斗;要是泥火盆里哪块火宣了,母亲就得用烙铁压实;给我心中烙印最深的一次,是一天早晨窗上的冰霜很厚,母亲拿起烙铁,上炕就“滋滋”烫化玻璃。我眼前一亮,打屋里一眼就瞅见外面的冰冷世界。可又一细看,烫化的窗上似乎象一个“中”字。后来有几次我看见烙铁便问过母亲为什么写“中”字?但每次她都一笑便打差过去了。至到现在,母亲已去世十多年了,可我还是没有读懂母亲生前用烙铁烫个“中”字的深远含义。
泥火盆除了取暖之外,还有很多别的功能。我们一小时,由于冬天黑的早,一到晚上就好围着火盆爆苞米花,用苞米吊子(秋天瓣苞米时留的,两穗的叶拴在一起,挂在屋芭上)的粒爆花。因苞米粒干的透,没有水分,能起大花,一爆就把火和灰一起崩起来,造得冒烟咕咚的,还挨父亲一顿骂;我们有时还崩黄豆,而黄豆就不爆花,没烟,但吃了之后就是直“当当”放屁;我们还烧土豆、烧豆苞,吃到嘴里比铁锅里烀的好吃多了;这些是我童年有印象的记忆,但还有没印象的事都是据姐姐讲的,她说我一小就爱玩火盆,拣起燃尽了灰杆就往嘴里吃,弄得嘴里都是灰面子,直干约,满脸还布满是灰道子,象似画了装,因这母亲没少数落姐姐不经心照料弟弟。虽然这些都是儿童的趣事,但最有刺激的应当数父亲在泥火盆里烧红辣椒,满屋都是又香又辣的味道,即爱闻又丁不住呛,呛得眼泪和鼻涕同时流到一起;还有父亲在泥火盆里用小铁盒炸的红辣椒酱,其味道让人也感觉到有几分“烧辣椒”的感觉,但刺激程度可就大大地减弱了。那苞米碴子云豆粥,拌上红辣椒酱,连我当时也能多吃上几口饭。
一晃“泥火盆”时代,告别我们已经很久远了,它在那个历史时期完整地画上一个句号。但我们每每地怀念起来“泥火盆”,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母亲火一样的深情,想起乡下采暖延革印证乡亲们生活的变迁。
今年六月六,我去乡下参加大姐夫66大寿生日宴,屋里地面有个窖门。大姐夫告诉我:这是“地热”。在室内挖个长2。5米宽1。8米深1。4米的地窖,四壁砌砖,上盖打上钢筋砼的板,留个下柴禾、掏灰的门。窖里再盘个烟道,直接走到外屋厨房的主烟囱;其尽头设个插板,控制烟量;窖内填碎柴禾、整柴禾都行,填一次能燃着几天,屋里的温度能达到20度左右;而这种采暖形式,且在全屯子基本达到普及,家家都是这种“地热”过冬,即卫生,又热乎。我望着眼前这个“窖盖”,心里久久平静不下来。之前我只知道城里楼房采暖都是采用地热的,而今天在我这脚下的“热源”才是名正言顺的“地热”。
于是,我把从打小记事时起一直到现在的记忆,编织一个回顾电影的程序,主线是顺着家乡农村采暖的变革一路浏览过来。从泥火盆到火炉子到暖气片,再到眼前的“地热”,一个个采暖方式的诞生,又一个个采暖方式的结束,宣告了农村生活环境步步攀上新的台阶,而不同时期的采暖方式,又浓缩了家乡不同时期“温暖火苗”的发展史。
2012/10/22
一束温暖的火苗的评论 (共 6 条)





- 路灯 审核通过并说 凝聚在泥火盆里燃烧,烤暖了儿女们滚烫的心。